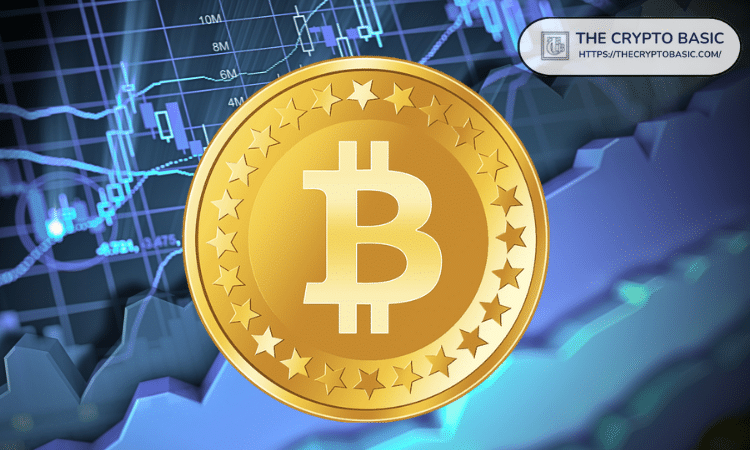原文: No One Wants to be the Reserve Currency
作者: Zeus
编译:Block unicorn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描述为美国的「过度特权」——美国王冠权力上的一颗明珠,赋予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我们听说,其他国家也对这一地位虎视眈眈,密谋推翻美元,夺取其特权地位。
然而,现实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真相远比直觉复杂:虽然美国经济的一部分——特别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从储备货币地位中获益匪浅,但这些收益高度集中,而成本却广泛分布在全国。这种结构性失衡使得储备货币角色在长期内本质上不可持续,无论持有者是谁。看似特权的东西,在仔细审视后,揭示出是一个镀金的牢笼——它带来的优势伴随着严重的结构性成本。
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问题体现在经济学家所谓的「特里芬困境」中,这一困境以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命名,他在 1960 年代提出了这一概念。其核心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给世界提供足够的美元用于国际贸易和储备,美国必须持续运行贸易逆差,本质上是通过出口美元来换取商品。
这些逆差虽然对全球货币稳定至关重要,但却逐渐侵蚀了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就业市场以及使美元最初具有吸引力的经济基础。储备货币发行国陷入国内与国际优先事项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永久解决,只能以不断增加的成本进行管理。
最明显的后果是美国制造业的急剧空心化。自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成为无可争议的储备货币以来,美国经历了深刻的产业转型。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60 年代的约 25% 下降到今天的不到 12%。曾经致力于生产的整个地区已经空心化,形成了臭名昭著的「铁锈地带」,并伴随着这一转变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动荡。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转型并非政策失败,而是美元全球角色的必然结构性后果。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资产时,该国在数学上必须消费超过生产,进口超过出口。其结果是,以消费繁荣为幌子,缓慢地去工业化。
外界通常认为,像德国、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出口强国,如果有机会,会急切地夺取储备货币地位。他们的的经济战略以出口驱动增长为中心,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他们当然希望本国货币占据美元的特权地位吧?
然而,这些国家始终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犹豫,不愿将其货币推广为美元的真正替代品。即使中国谈到人民币国际化,其实际政策仍然谨慎,且范围有限。
这种犹豫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对相关成本的清晰认识。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来说,储备货币地位将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对其货币的需求增加将推高其价值,使出口更加昂贵,进口更加便宜。由此产生的贸易逆差将破坏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出口驱动模式。
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历提供了一个警示。随着日元开始国际化和升值,日本政策制定者对其出口部门的影响有所顾虑。1985 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最终终结了日本的经济奇迹,开启了其「失落的三十年」。密切关注这段历史的中国,自然也不愿重蹈覆辙。
对这些国家来说,当前的安排提供了更好的方案:它们可以维持低估的货币以促进出口,同时将美元顺差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实际上是将资金借给美国人购买其产品。这种美元循环利用他们能够保持出口优势,同时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美国消费提供资金。
与此同时,它们免于提供全球流动性、管理国际金融危机或在国内需求与国际责任之间的矛盾中挣扎的负担。他们享受了美元体系的好处,却无需承担其成本。
或许,最能证明储备货币地位并非如其所描绘的那样丰厚的奖励的证据来自美国自身。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自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质疑「过度特权」是否值得其国内成本。
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表达了这一转变。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其第二任期内以更大的力度再次出台,直接挑战了维持美元霸权的机制。通过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广泛关税(特定国家适用更高的税率),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在表明,美国不再愿意为了储备货币地位而牺牲其工业基础。
当特朗普宣称「关税是字典中最美丽的词」时,他标志着美国优先事项的深刻转变。其目标明确:减少贸易逆差,即使以破坏维持美元主导地位的机制为代价。
这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反常之举。贸易怀疑论已日益成为两党共识,各政治派别的知名人士都对自由贸易的正统观念及其对美国工人的影响提出质疑。数十年来,维持美元霸权可以证明美国国内去工业化是合理的,而这种共识都正在左右两派的心中摇摇欲坠。
要理解为何在无人愿意占据核心地位的情况下,现行体系依然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为不同参与者创造的不对称利益。
对于新兴经济体,美元体系提供了一条成熟的发展路径。通过维持低估的货币并专注于出口,从韩国到越南的国家推动了其工业发展。制造业就业为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奠定了基础,而技术转移加速了现代化。这些国家乐于接受美元主导作为这一发展模式的入场代价。
对于瑞士、新加坡和英国等金融中心,美元体系创造了丰厚的机遇,而无需承担储备货币地位的全部负担。它们可以参与全球美元市场,为美元流动提供金融服务,并在不遭受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面临的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捕获巨大的价值。
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成本被消费者的好处部分掩盖。美国人享受进口商品的低价、便捷的信贷以及比其他情况下更低的利率。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部门通过管理全球美元流动捕获了巨大的价值。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在历史上超过了工业空心化这一不那么明显但深远的成本。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一种储备货币能永远持续。从葡萄牙雷亚尔到荷兰盾再到英镑,每一种全球货币最终都因支撑其经济基础的侵蚀而让位。美元当前的困境表明这一历史模式仍在继续。
我们当前时刻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一个国家似乎急于接过这一重担。最常被提及的潜在继任者中国,对全面国际化人民币表现出了显著的犹豫。欧洲的欧元项目在缺乏财政联盟的情况下仍不完整。日本和英国则缺乏必要的经济规模。
这种集体犹豫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主要储备货币显示出退出其角色的迹象,但没有明显的替代者准备就绪。
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政策可能加速这一过渡。通过优先考虑国内产业而非国际金融安排,政府实际上是在表明,美国将不再接受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需的结构性贸易逆差。然而,没有这些逆差,世界可能面临美元短缺,这可能严重限制全球贸易和金融。
如果当前的储备货币安排已变得不可持续,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这一过渡会有多混乱?
我们应该承认,从一种全球货币秩序过渡到另一种在历史上往往是混乱的,常常伴随着金融危机、政治动荡,有时甚至是战争。从英镑到美元的转变并非计划或有序的——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混乱中浮现的。我们应该预期未来的任何过渡不会少于这种动荡,除非我们有意识地设计以实现稳定。
最常讨论的替代方案是一个多极货币体系,其中几种主要货币共享储备地位。这将把利益和负担分配到多个经济体上,可能减轻任何一个国家维持过度赤字的压力。
然而,多极体系会带来自身的挑战。流动性分散会增加交易成本并使危机应对复杂化。竞争性货币当局之间的协调问题在金融压力期间会加剧。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只是将特里芬困境转移到多个肩膀上,而不是解决其核心的根本矛盾。
与其关注具体的实施方案,不如让我们思考一下,理想的储备体系及其转型应遵循哪些原则——该体系能够解决核心悖论:储备货币地位带来的成本是任何国家都不愿承受的。
1. 集体治理而非单边控制
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根本问题是国内需求与国际责任之间的不可避免冲突。理想的体系会将这些功能分开,同时允许国家继续作为体系治理的利益相关者。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变得无能为力——恰恰相反。它们将在直接服务于共同利益的体系中获得更有意义的集体影响力,而不是受制于单一国家的国内政治压力。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参与;它意味着改变参与方式。
2. 原则性供应管理
当前体系实际上包含一个值得保留的关键特性:扩展货币存量并出口以满足全球需求的能力。这种扩展能力对全球经济运作至关重要。问题不在于扩展本身,而在于谁来承担扩展的成本以及如何治理。
理想的体系将保留这种扩展能力,同时增加当前体系缺乏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对称的收缩。这种平衡方法将保留当今体系的优点,同时解决其结构性弱点。
这并非要发明全新的机制,而是要实施几十年来人们理解但由于政治限制而未能实施的原则。
3. 吸收式过渡而非取代
或许最重要的原则是,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必须吸收而非攻击当前体系。被实体持有的约 36 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不能简单地被抛弃,否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损害。
理想的体系将在过渡期间为这些资产创造持续需求,允许渐进演变而非破坏性革命。这不是要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而是要确保体系演变过程中的连续性。
当前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实际上将从这种方法中受益——获得使其经济向生产再平衡的能力,而不会引发损害所有人利益的债务市场崩溃。
4. 危机韧性设计
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重要的是体系如何应对这些危机。当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酌情干预,政治考量往往影响干预的时机和规模。
理想的替代方案将纳入预定的、透明的机制,以在压力期间稳定市场——提供紧急流动性,防止恐慌连锁反应,并确保关键市场即使在个人私利可能驱动破坏性行为时也能正常运转。
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并未消除国家层面的酌情危机应对。主权货币将保留其完整的危机管理工具包——各国央行仍可进行紧急操作,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或根据需要应对国内金融压力。不同之处在于,国际储备层将以更可预测、基于规则的机制运作,减少对单一国家决策的依赖以维持全球稳定。这创造了一个互补的双层体系:可预测的国际协调与灵活的国家应对并存,各司其职。
5. 管理下的升值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稳定但可控升值的储备资产为整个体系带来一定的好处。它将为中央银行逐步增加持有量创造自然激励,同时仍允许出口驱动型经济正常运作。由于这些出口经济体已对其货币相对于美元进行管理,它们可以继续对新的储备资产采取这种做法。
货币演变中最危险的时期是过渡阶段。在这里,设计以实现稳定至关重要。转变可能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
初步采用:从互补共存而非取代开始,新体系将在最小化干扰的同时建立信誉。
储备多元化:各机构,尤其是中央银行,将逐步将新资产纳入其储备,从而降低美元集中度,同时又不引发市场恐慌。
结算功能发展:随着流动性和采用率的增加,该体系可以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国际贸易的结算功能。
成熟均衡:最终将出现一种新的平衡,各国货币将保持其国内职能,而国际职能则转向更中立的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美元将保持重要性——只是逐渐摆脱同时服务国内和国际需求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代表的是演变,而非革命。
无论理论替代方案设计得多么完善,从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过渡都面临巨大挑战。美元在全球贸易、金融市场和中央银行储备中根深蒂固。突然的变化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债务违约和市场失灵,并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负责任的过渡需要建立体系之间的桥梁,而不是摧毁它们。那些鼓吹美元崩溃的革命性方法,恰恰可能造成货币体系本应避免的经济灾难。尽管现行制度多么有缺陷,但数十亿人仍依赖其持续运作,即使在替代方案发展的同时。
最可行的前进路径是渐进演变,而非突然革命。新体系必须通过实用性而非意识形态证明其优势,通过正向激励而非强制性干扰获得采用。
任何货币体系的最终衡量标准不是其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是其对人类繁荣的实际影响。当前储备货币安排创造的不对称利益和负担越来越显得不可持续。一个设计良好的替代方案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创造更平衡的繁荣:
繁荣问题最终在于平衡稳定性、适应性和公平性——创建一个既能为长期规划提供足够可预测性的体系,又能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并比现行制度更公平地分配利益。
关于储备货币地位的真相包含着重要的细微差别。并非真的无人想要它——金融部门的某些部分无疑会从中受益,并因此支持它。更确切地说,利益是集中的,而成本却分布在更广泛的经济中。这种固有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它无论哪个国家承担重担,都无法长期维持。
特朗普的政策表明,美国可能不再愿意接受这些分散的成本来维持这一全球角色。然而,该体系之所以得以延续,是因为尽管存在缺陷,但每个人都依赖于有人来履行这些职能。
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在其他国家几十年来一直被指责「操纵」本国货币以逃避美元角色之后,美国本身可能是最终摆脱储备货币地位负担的国家。这既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机遇——既有无序转型的危险,也有设计出从根本上更好的体系的机遇。
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哲学性的——重新设计全球金融的基础,以服务于人类繁荣而非国家利益。如果我们成功,我们或许能最终解决这一悖论:任何单一一个国家都无法持续提供基本全球货币功能。